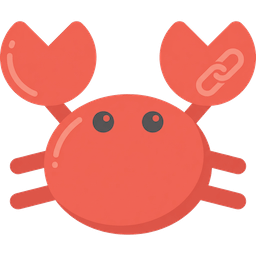在贝尔·伯登(Belle Burden)的回忆录《陌生人》(Strangers)中,她记录了自己婚姻的终结。一切发生得猝然:直到从一个陌生人的语音留言中得知丈夫不忠之前,她对生活的裂痕一无所知。伯登与丈夫在翠贝卡(Tribeca)拥有一套公寓,在马萨葡萄园岛(Martha’s Vineyard)有一栋别墅。他们曾享受在心仪餐厅的浪漫周五晚餐,孩子们在精英私立学校茁壮成长。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经过精心打理与提炼——理想化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。“我爱他的衣服,爱他上班时的装束,”伯登写道,“深蓝色或炭灰色的西装,挺括的衬衫,配上一条略带色彩的领带……那是一个负责任、值得信赖的男人的行头。”他们同样反感汉普顿(The Hamptons)那种充斥着“攀比、盛装和拥堵”的“现代版本”,而在葡萄园岛的俱乐部里,他们如鱼得水,那里的成员“穿着亚麻西装和彩裙聚在一起参加鸡尾酒会”。甚至连微小的细节都经过精调:伯登写道,尽管丈夫忙于对冲基金业务,但他“从九月就开始搜集万圣节糖果,寻找那些难得一见的酸味糖果品牌来填满家里的糖果碗”。
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像伯登那样光彩照人,她是范德比尔特(Vanderbilt)家族的后裔,也是时尚偶像贝比·帕利(Babe Paley)的孙女。(她记得当她和丈夫搬到一起住时,她带去了年轻时的家当——“一张红木床,祖父的书桌,还有父亲拍摄的莎莉·曼 [Sally Mann] 的照片”。)尽管如此,当我们读到她如何爱上他时,依然能产生共鸣:“当我看到他自信地走下公寓后面宽阔陡峭的阶梯,在为我撑住沉重的门时顺手将条纹牛津衫塞进裤腰,我想:我要嫁给这个男人。”即便我们只读过 F. 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(F. Scott Fitzgerald),而未曾生活在他所描述的精英世界里,他那种沉稳、优雅、又带着一丝放纵的独特视角,也足以令我们沉醉。或者,我们可能偏爱另一种愿景:泰勒·斯威夫特(Taylor Swift)在《Style》中呈现的詹姆斯·迪恩(James Dean)式“乖乖女”审美,亦或是《黄石》(Yellowstone)中贝丝(Beth)与里普(Rip)那样的格调。
虽然风格可能流于表面,但在理想情况下,它反映了一些更本质的东西——知识、判断、意图和洞察力。简言之,就是“品味”。“品味主宰着每一种自由的人类反应——相对于机械的反应而言,”苏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)在 1964 年的《坎普札记》(Notes on ‘Camp,’)中写道,“人的品味、视觉的品味、情感的品味——甚至在行为、道德以及‘思想’中都存在品味。”在文章中,桑塔格探讨了“坎普”(Camp)的概念,欣赏这种风格需要具备“坏品味中的好品味”。而在今天,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也在谈论“研究品味”:他们希望创造出像顶尖人类那样具备直觉的算法,能判断哪些问题有趣,而哪些会走进死胡同。我们利用品味去感知、去决策、去思考。
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品味是我们所“做”的事——像是我们可以挥舞的工具。然而,情况往往恰恰相反。“要么你自己思考——要么别人替你思考并夺走你的权力,扭曲和管教你天然的品味,让你变得文明而贫瘠,”尼科尔·戴弗(Nicole Diver)在菲茨杰拉德的《夜色温柔》(Tender Is the Night)中沉思道。世界总是在告诉你该喜欢什么;因此,品味是值得怀疑的。你何时是在表达真实的自我,又在何时任由他人重塑自己?当你走进布鲁克林一套布置精美的公寓,你会赞赏主人的品味。可当你走进十套一模一样的公寓时,你会开始怀疑:拥有完美的品味是否实际上意味着根本没有品味。
品味具有欺骗性或分散注意力的隐忧,似乎笼罩着每一个涉及它的故事。在《陌生人》中,伯登纳闷自己为何没能察觉丈夫的不快乐,也追问他为何连自己也瞒过了。“我以为我很幸福,但我并不幸福,”他告诉她,“我以为我想要这种生活,但我并不想要。”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告别方式。然而,后来一位朋友告诉伯登,离婚解放了她真实的人格,揭示了一个“更轻盈、更自在、更放松”的她。“你似乎正在摆脱一整套更宏大的文化标准,摆脱某种外部强加的‘你应该成为谁’的观念。”有品味地生活需要做出许多微小而正确的决定,成功做到这一点会让你产生一种正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错觉。但精心雕琢“如画般生活”的风险在于,你可能会因此忽略生活的“全貌”。
文森佐·拉特罗尼科(Vincenzo Latronico)的小说《完美》(Perfection)的主人公阿丽娜(Anna)和汤姆(Tom)是生活在柏林的“创意专业人士”。“他们的具体头衔因工作而异,”拉特罗尼科写道,“网页开发、平面设计、在线品牌策略”——核心在于他们创造“差异”。当一家新的精品酒店开业时,它需要在拥挤的品味版图中传达其独特性。阿丽娜和汤姆通过色调的微调或字体的精妙运用来实现这一点。“他们的风格简约、私密,符合一种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的审美,”拉特罗尼科解释道——那是从“每一家高级汉堡店和音乐会海报”中散发出来的熟悉的“随性酷感”。
这对夫妇的好品味从屏幕流向物理世界,再流回屏幕。在社交媒体上,他们看到无尽的网格,里面满是通透的公寓,“落地窗前、胶合板书架上、鱼骨纹拼花地板旁摆放着迷人的植物”。很快,他们的公寓也成了一座温室——“植物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,这成了一项全面发展的技能,”拉特罗尼科写道——这丰富了他们发布的照片。当他们在网上挂出公寓供游客租赁时,这种品味得到了变现。同样地,在多年重复制作三明治和意面酱之后,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成为了严肃的厨师。朋友家的晚餐突然出现了“撒满种子和水果的精致沙拉”,每一道菜都伴随着“一阵赞美和技术性的点评”。拉特罗尼科指出,“他们的兴趣并非源自精明营销人员的植入,而像是通过渗透作用产生的,因为他们观察着周围那些微小的差异。”作为有品味的一代成员,“他们都在一起学习”。
收集黑胶、去 Berghain 俱乐部(clubbing at Berghain)、考虑多边恋(polyamory)——这很酷。但阿丽娜和汤姆并不感到自由。他们被困在了自己亲手构建的品味矩阵中。毕竟,正是他们自己的好品味最初促使他们逃离偏远的家乡来到柏林;而当新涌入的酷感猎寻者推高了城市的消费时,又是品味驱使他们前往里斯本(“新的柏林”),期望重复这一循环。问题在于,数据比人跑得快。当晚宴照片可以瞬间传遍“地球的另一端,在低地轨道上弹射或在深海海脊间穿梭”时,有意义的差异便无法持久。在里斯本,“一切都不同了,这正是他们想要的;然而,一切又莫名地一模一样。”
《完美》中带有一种科幻色彩,但它准确记录了现代品味是如何发挥作用的。品味是一股全球性力量,驱动着移民,改变着投资,并将我们划分成不同的群体与部落。因为它已经被高度技术化,现在它给人一种统一感、无处不在感——像是一股席卷我们却从未破碎的浪潮。哲学家们描述了“昂贵品味的问题”:今天的奢侈品会变成明天的必需品。对于阿丽娜和汤姆来说,这种动力导致了流亡。他们被赶出了出生地,又由于价格昂贵而无法在向往之地落脚,在能够负担得起的地方又无法获得满足。在小说的最后一幕,尽管他们的品味处处可见,但他们已成了无国籍的游民。
海伦·德维特(Helen DeWitt)的中篇小说《英国人懂羊毛》(The English Understand Wool)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(Marguerite)也被品味所困。她一生都浸淫在一种超乎想象的奢华与精致氛围中。她的家族居住在马拉喀什,但她雇了一位从巴黎飞来的老师教她钢琴。当玛格丽特的母亲需要一套新套装时,她会飞往苏格兰,从“一位真正的天才织工”那里购买花呢。玛格丽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变得 mauvais ton——即品味低俗。在斋月期间,她和父母会为了仆人们去度假,尽管薪水照发。“让正在斋戒的人服侍是 mauvais ton,”玛格丽特解释道,“以宗教禁忌为借口削减他们的工资同样是 mauvais ton。”
玛格丽特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——说出这件事也是 mauvais ton——她不仅被迫离开那个斯文特权的世界,还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。她最终来到了纽约,签下了一份丰厚的回忆录合同。但她的编辑贝瑟尼(Bethany)对草稿并不满意。“嘿,玛格丽特,”贝瑟尼写道,“背景铺垫太多了,让读者一直等不到重头戏。”贝瑟尼认为,这本回忆录应该是一部充满猎奇色彩的爆料书;她建议找个代笔,可能会把文字“敲打成形”。或者,她想知道,“如果咱们见面聊聊,我直接用手机录下来,这样至少能有点现成的素材,你觉得会有帮助吗?”
最终,正是玛格丽特的好品味让她没有屈服于压力,拒绝写出一份庸俗的人生账本。这关于品味为何有价值的一个颇为可信的理论: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小事当然很美好,但品味的展现实际上是为未来更重要的表现所做的排练。如果你在今天磨练品味,那么日后当你站在聚光灯下时,你就已经有了标准。当你迎来决定性时刻,你可能会汲取过往在洞察、得体和美德方面的经验。(当然,这个理论的反面——坏品味暗示着你表现不佳——就不那么讨喜了。)
我们的品味往往比我们自身更优秀,这并不罕见。当我们年轻时,我们可以迅速变得极有品味;我们可能知道该读什么,却不知道该如何行事,或者我们可能轻易地被“酷”所迷惑。(而当我们年长时,我们或许能负担得起那些我们并不懂得欣赏的雅致之物。)在简·奥斯汀(Jane Austen)的小说中,聪明且有品味的年轻女性常常爱上表面相似的青年,却发现追求者的品味仅流于表面;令她们倍感羞愧的是,她们意识到自己同样是品味有余而智慧不足。但奥斯汀笔下的女主角在幻灭之后重振旗鼓。既然此前已经断定几乎一切皆为 mauvais ton——“我越看这个世界,就越对它感到不满,”伊丽莎白·班内特(Elizabeth Bennet)在《傲慢与偏见》(Pride and Prejudice)中如是说——她们便致力于进一步开发自己的官能,让自己配得上已经培养出来的品味。这是支持品味的另一个理由:它是我们自我提升的主要机制之一。
然而,将品味主要视为一种达成目标的手段是不完全正确的。在德维特的短篇小说中,玛格丽特是把品味本身当回事。她绝不会如此粗俗地去追求什么“自我提升”。相反,她真正关心爵士乐表演是否有正确的摇摆节奏。“英国人懂羊毛,”德维特写道,“法国人懂葡萄酒、奶酪、面包……德国人懂精密、机械……瑞士人懂谨慎。”这种理解关注的不是自我,而是事物本身。这就是品味的悖论。你的品味可以传达很多关于你的信息,但它实际上与你无关。拥有好品味可能会指引你走向美好。然而,当你认为自己很“好”时,你就掉进了品味的陷阱。 ♦